封面故事/专访百岁王鼎钧 谈写作、说野心、聊忏悔 (6QA完整版)
人称「鼎公」的王鼎钧自1963年出版首作以来,60多年笔耕不辍,前有反映人性与洞见的「人生三书」,熔铸毕生记忆、显一代中国人因果纠结与生死流转「回忆四书」,近有由他亲自打捞,在今年出版繁体版的《江河旋律》,在新冠疫情期间及之后,他也以键盘代笔,孜孜不倦,与后生程奇逢「轮流发球」,合著《四手联弹》,针对同一主题各抒己见,显示世事、人情与利害的不同面与质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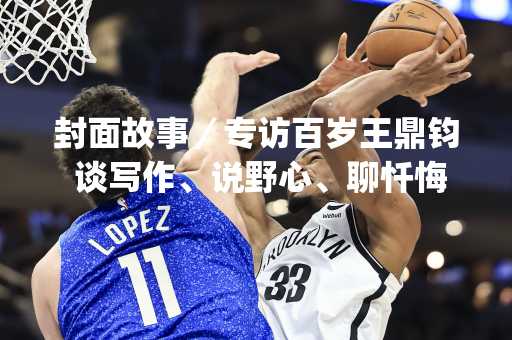
在王鼎钧将满百岁之际,他与夫人王棣华一道来访世界日报纽约总社,回顾并畅叙自己的创作生涯。
少年时,王鼎钧弃学从军,曾经历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,在1949年到台湾后,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「险峻」的文学江湖。1978年他来到美国纽约后,从此「侯门一入深似海」。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调动时空,前后写了17年,几经修订下完成了《回忆录四部曲》,「把痛苦的记忆写得不痛苦,也不把痛苦再转嫁给读者。」
作家张晓风称王鼎钧为「一代中国人的眼睛」,张大春为王鼎钧冠「文心」二字,结论却指是国家辜负了王鼎钧,然而,王鼎钧却在访谈中说,他这一代人,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,战争反淘汰时,他万劫归来,倘若加减乘除,国家并不欠他什么,是「去臣无怨词,忧谗畏讥」。但对于国家,四海漂流的他,是处处非家处处家,只有路,没有屋,「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国家,但是最好只有一个国家,国家多了可能是一种折磨」。
有读者评论,有作者过了中年的巅峰时期便开始衰败,而王鼎钧却是例外,在步入老年,他创作的「左心房漩涡」等作品是发力之作,而到古稀之年,他更是进入了文学创作的「冲刺阶段。」在超越与升华了文本乃至生命经历中的痛苦以后,王鼎钧似乎也没有作家所需要面临的「痛苦的瓶颈期」。相反,文字与文学为他持续带来隐密的「甘甜」,文字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,搭配不可计量的音韵变化,让他上瘾成癖,「贪得无厌」,贯穿始终又屡屡出新地书写。是文学让他安住。
以下是访谈内容:
「特别关心文学 造了许多口业」
问:先从《江河旋律》聊起。我们从出版社及隐地先生的书序了解,这本自选集先是2020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,无序无后记,低调极简;继由台湾的「尔雅」于今年出版繁体版,在台北的国际书展发表。集子分为三类:美文选、变体选、杂文选,过程中,鼎公亲力亲为。您说,临江打捞,希望能为读者留下。可否先请鼎公介绍您在《江河旋律》中的选文标准,过程之中,有哪些特别感触希望传递给读者?
王鼎钧:这本选集是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主编付如初女士的邀约而成,《江河旋律》这个书名代表我勤奋创作勇敢探索的年代。美文的「美」指美感,文章以表现美感为目的,美感是艺术欣赏的一种境界,近似我们古人所说的陶然、欣然。「变体」的「体」指体裁,文学作品的体裁有诗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,变体是在散文中使用了小说、戏剧的技巧,是一种美丽的错误,有人称为「兼体的散文」,有人称为「散文的出位」。最后一项是条杂文,祖师爷鲁迅的遗风余脉渡海而来,行文如厨房的杂碎,马戏团的杂耍,宗教的杂念,无可归类只有自成一类。
我的野心是写美文,我认为这是文学创作的正果,然后是出位兼类写变体的散文,这是传统的延长,文化遗产的增加。可是事实上我一直写杂文,1952年,我在台北进入中国广播公司担任编撰,正式卖文为生,直到2008年,这70多年我写了难以计数的杂文。我以写作谋生,文稿按字计酬,杂文能大量生产,计时完成。杂文的「艺术含金量」很低,除了鲁迅以外,几乎没有谁可以名世。
晚年,我写过一篇文章〈我后悔说了那些话〉。那时台湾的公务员对上门办事的平民百姓,尤其对乡下人,态度十分恶劣,你如果送上红包,他马上和颜悦色,我说他们「卖笑」。那时办任何事都得找关系,托人情,同样一件事情,张三托人办不通,李四送红包办成了,钞票上面印著孙中山的肖像,我说李四是托国父出面,当然如愿。那时号称威权时代,民意机构的权力缩小,失去监督政府的作用,政府为了维持宪政的形式,仍然用高薪厚禄养士,我们讥讽他们有些是「卖手的」,在法案需要通过的时候举手表决,有人是「卖嘴的」,在审议法案的时候发言支持,有些人是「卖屁股的」,按时坐在座位上凑足法定人数。这些话都是杂文腔调,博得满堂采声,我深感忏悔。
我对文学特别关心,在这方面造了许多口业。50年代,教育部设置了台湾第一家文学奖,开始两届的得奖人都是从文化界「淡出」的老师宿儒,我说,这样的文学奖何必要办,不如每年给李白、杜甫烧一些冥纸算了。我说台湾有人居间为政府拉拢作家,可称为「文学掮客」,有老年年长的女作家指东画西,喜怒无常,可称为「文学婆婆」,年轻女作家搬弄口舌是非,可称为「文学小姑」;某人有作家和官员两种身分,以文学伺候政府,又以官员身分君临作家,我称之为文学太监,有人专卖赤裸裸的性爱小说,借色相宣传造势,我称之为「文学老鸨」。诸如此类,口不择言,罪孽深重,我深深忏悔。
「写作是痒、是瘾、是朝思暮想」
问:鼎公出版著作逾40种,文类甚多,散文、评论,乃至小说无不涵盖,「人生三书」及「回忆四书」俱为代表。您被誉为「一代中国人的眼睛」。张晓风女士特别提及鼎公所著「活到老,真好」,鼎公自是经过颠沛、流离、故乡他乡,透过作家之眼为时代见证,更留下丰美作品。鼎公60多年笔耕不辍,真的没有经历过所谓作家的瓶颈吗?
王鼎钧:不瞒您说,最初,我是拿写作当做一门手艺来学习的。写作是由「内在的构意」到「外在的构词」,需要使用一种工具,就是语言文字,如何使用工具要经过学习,「辞达而已矣」,我的了解就是你完全掌握这种工具了,完全发挥工具的性能了,把「构意」和「构词」之间的高墙拆除了,我在学习中爱上了咱们的文字。
中国文字是那么可爱,字形可爱,字音可爱,字义可爱。冩作是文字的排列组合,中国字号称方块字,使用起来灵活方便,字靠著字、字连著字、字叠著字,爱得你要死。每个字是一个精灵,一道符咒,排列组合的变化无穷无尽,使你上瘾,使你成癖,使你贪得无厌,你把心一横「我就这样了此一生罢!」如此这般,做成一个贯彻始终的作家。
前贤说每个方块字像一块砖,可以筑成宫殿,作家像一个建筑师;我说每一个方块字像一幅图画,可以连成大地山河,作家像一个画家或者电影导演。方块字除了一字一形,还有一字一音,这一个字像一个音符,作家写作的时候像一个音乐家,他排列声音。中国字有四声,有轻声变调儿化韵,声音有轻重长短高低强弱,变化也是不可胜计。作家使字音彰显字义,字义强化字音,两者相得益彰,运用之妙存乎一心,内心自有一种秘密的甘甜。「甘」是美感,「甜」是快感,所谓得失寸心知,就是暗自回味这种甘甜,甜到心里,甜到梦里,你乐不思蜀,乐此不疲,这才做成了一个作家。
我常常劝写文章的朋友,文章不能逢年过节写一篇,不能儿娶女嫁写一篇,不能等到日食月食写一篇。写作不是你长周末去钓了一条鱼,不是百货公司大减价去买了个皮包,写作是你兼了个差,天天要签到值班,写作是你养了个宠物,随时想抱一抱,摸一下,看一眼,为了它早回家,晚睡觉。写作是一种痒,手痒,心痒,写作是一种瘾,就像烟瘾酒瘾。写作是朝思暮想,千回百转,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。
王鼎钧说,「我以前只知道悯人。同情所有的人,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天?后来才晓得,这个悲是同情,不是悲哀。有很多事情,老天爷也不愿意它发生,但是老天爷也没办法啊。这个境界叫做悲天。」(记者李芊芊/摄影)
「以前只知悯人 不知为何悲天」
问:您曾说,60年代后期,70年代初期,您决心以文学立命,设法「一步步使职业与文学脱钩」,何以下这样的决心,您又是怎么做到「脱钩」的?也有许多年轻人,有这样的转型期许,您对他们的建议是?
王鼎钧:我的一位老师说过,文学并非专门的学问。我的理解,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生命,万物皆备于我,六经皆我注脚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依据这个了解,我把作家分成三大类,有一党的作家,有一国的作家,有人类的作家。作家可以党同伐异,各为其主。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国人的立场上表现人生、批判人生,超越党派,超越地域,超越阶级,当然超越自已的利害祸福。这样的作品仍然很难成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,更上层楼是「人类的作家,居高临下。悲天悯人。我以前只知道悯人。同情所有的人,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天?后来才晓得,这个悲是同情,不是悲哀,同情老天爷啊,为什么要同情老天爷?有很多事情,老天爷也不愿意它发生,但是老天爷也没办法啊。这个境界叫做悲天。
我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,基督教没有悲天,基督教的上帝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和同情。你说你同情上帝,对上帝是一种侮辱。但是我后来还受佛教影响,佛教对于作家有帮助,佛教里头有悲天,佛不愿意发生的事情照样发生,祂并不能够使那些事情不发生。这个时候佛是很痛苦的。
人类的作家最后要有这个境界,在他的心目中众生平等,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他把作品经营成高级象征,不管读者的国籍、种族、信仰,作品对他都有意义。众人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,每一个人的痛苦也是众生全体的痛苦,读者一旦进入这样的作品,也就进入了共同的人性,营造共同的谅解。
所谓与职业脱钩,意思是不再把文学当作使用工具的技能,不是指作家转业。我年轻的时候梦见在稿纸上画钞票,一面画一面担心有人看出来是伪钞。我要做另一种梦,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梦?我还没有做过。至于转业,每个人都有他婴儿时代的鞋子,少年是诗人,青年是革命家,中年是商人。另有高就当然很好,我不劝人和我一样。
「故乡是我初恋 纽约是我婚姻」
问:您的作品言浅意深,经常饱涵丰富的各种知识与常识,更多寓言式故事信手拈来。近日读《四手联弹》,更发现您对时下资讯掌握亦相当快速,例如不过数年前的电视剧《与恶的距离》也出现在您的分析之中。请您分享身为作家对于知识、常识、资讯收集,乃至想像力与理想化是如何编织运作,及其所扮演的角色。另外,您曾论及纸媒与网路的未来,对纸本仍乐观吗?
王鼎钧:这些年我不断公开我的写作经验,出了好几本书,自己写不好,希望别人能写好。答复刚才这个问题,千言万语难尽,长话短说,也可以总而言之,无他,写作不能只是知识,必须是行为。当年某大学请马可吐温演讲,题目是「怎样写小说」,凭他的盛名号召,满堂座无虚席,他登上讲台,抛出一个问题:你们是不是都想写小说?台下一齐举手,他再问一句:「你们不赶快回家写小说,坐在这里干甚么?」
这一点意思,我为中学生的作文写过一首歌:作文真痛快 心里的话写出来/是鸟就要叫 是花就要开/我叫得比你响 我开得比你快/来来来 中学生好自在/小文豪大天才/一窍通了百窍开/条条大路通作文/我的秘诀你不用猜
关于「论及纸媒与网路的未来」我未说过对纸媒充满乐观,但我说过纸媒不会「消灭」,文化有更新的机能,也有储存的机能,某种艺术形式一经成立,永远存在,人造纤维并未消灭蚕丝,织布机并未消灭刺绣,塑胶并未消灭瓷器,电影并未消灭舞台剧。家家户户「鸳鸯绣就凭君看」的盛况不再,刺绣从商品成为艺品,仍然存在。我能说的只有这么一点点。
王鼎钧茶余饭后欣赏太太王棣华的花艺。(本报资料照/记者许振辉摄影)
问:前面提及颠沛流离,您自中国大陆到台湾再到纽约的经过,自是两岸关系一段不堪回首的时代缩影,鼎公自身也曾身涉国共矛盾之中,在作家张大春新近演讲帮大家回顾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经过。张大春以「文心」形容鼎公的谦冲,似是以文学升华;但他的结论是国家辜负了您,甚为沉重。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段人生与历史?
王鼎钧:1931年,九一八事变发生,我七岁,开始有国家观念。我受的教育是国家多难,这一代人要救国,救国需要牺牲,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。战争来了,我经过对日抗战、国共内战,战争是反淘汰,我苟全性命,万劫归来,倘若加减乘除,其中总有对不起国家的地方。国家并不欠我什么。说到这里,我的大白话不够用了,借用文言,「去臣无怨词,忧谗畏讥」。
我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对不同的访问者说过,我这一生混到三个国,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,还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。人生在世不能没有国家,但是最好只有一个国家,国家多了可能是一种折磨。我的问题是有三个国,没有家,四海飘流,处处非家处处家,用台语来形容,我这样的入「只有路,没有屋。」我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、对不同的访问者说过,中国生我,台湾养我,美国用我。故乡是我的初恋,刻骨铭心,纽约是我的婚姻,侯门一入深似海。
我这一生只好稀里胡涂,不求甚解,但是下一代呢?我不止一次告诉孩子们,你们是法律上的美国人,血统上和文化上的中国人,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,但是保持中国的特色。爱中国,效忠美国,叶落未必归根,风媒水媒,分散也是繁殖。这也算是「极无可如何之遇」了,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?
王鼎钧(左)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,夫人王棣华(右)除了提醒「老伴」喝水,全程「盯著」老伴,仔细聆听她口中的「怪人」发言。(记者张宗智/摄影)
「看见世报转型 增进族群和谐」
问:亦不免俗请问您的养生之道,以及您的创作习惯,有无特殊环境。据称,您也是个夜猫子。
王鼎钧:既然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冲突」,养生就是自私,所以我们瞧不起延年益寿。运动?太可笑了,整天劳苦的还需要打太极拳?到了50年代,我们还认为胆固醇是一种心病,缺乏维他命是商品推销的广告。我那一代都在险境中生活,幸而世界日报有一大特色,天天推出C3健康版、D6橘世代、D2养生版,告诉我们怎样吃饭、怎样吃药、怎样吃菜、怎样睡眠,我才知道过去都做错了,魔鬼藏在细节里,世界日报教育了我、保护了我。养生之道也是千言万语,总而言之看世界日报。
问:您在1978年来到美国以后就与世界日报有非常多的联系,也有许多文章都发表在联合报及世界日报之上,世界日报明年也将迎接50周年。您对世界日报有著什么样的勉励与期许?
王鼎钧:我从1978年来到美国,就到世界日报来报到、拜访各位,也得到了许多的照顾,也可以说,我是先知道纽约有个世界日报,我才敢来。我也看见世界周刊的创办,世界周刊包容量大,更配合移民的需要,指导我们在美国的生活。因为我们来美国也很需要出去学习,所以非常感谢。
我也看见世界日报的转型,从台湾的子报变成国际性的大报。纸上涵盖了两岸读者关心的内容,这一点不容易,不著痕迹,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。一开始,我还记得有部分读者不能接受,比如说在加州举行的奥林匹克 (编按:1984年洛杉矶奥运),大陆的选手李宁得了金牌,世界日报头题报导,我们很赞成,但是有少数读者不赞成这样做。但是时间久了,他们也都接受了世界日报的包容量,潜移默化增进族群的和谐。
世界日报明年将迎接50周年,王鼎钧(中)向世界日报社长张宗智(左)及记者郑怡嫣表示,他1978年来到美国,就到世界日报「报到、拜访」,也看见世界周刊的创办,也看见世界日报的转型。(记者何振忠/摄影)
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,是一部近代史诗。一段接一段的故事,有如精采有趣的章回小说。从民国初年到1978年,历经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烽火年代,在台湾见证了台湾文学、报业、广播、电视的发展,以及白色恐怖。
《昨天的云》是王鼎钧「回忆录四部曲」第一部。他在序中写首:我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,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。「第一本书」指自传式的小说,「最后一本书」指作家的回忆录。我曾经想写「第一本书」,始终没写出来。现在,我想写「最后一本书」了。以下摘自本书:我不是在写历史,历史如云,我只是抬头看过;历史如雷,我只是掩耳听过;历史如霞,我一直思量「落霞孤鹜齐飞」何以成千古名句。……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,使片云再现,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。──王鼎钧
《怒目少年》是王鼎钧「回忆录四部曲」的第二部。他在序中说:中国人生了气,有时候像滚水,有时像火山。抗战军兴,中国人蓄怒待发,出气的对象有变化,先对外国,后对本国。许多事我或在局外、或在局内,许多人我或者理解、或者迷惑。许多人,包括我在内,我们不知道何时,何故发生这种载舟覆舟的变化,我们不是秋风未动蝉先觉,而是秋风已动蝉先落。出入于两种怒气(对外国和对本国)之间的我,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,构成这本书的内容。它记述由1942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,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,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。以下摘自本书:在《怒目少年》那样的年纪,开始窗隙窥月,雾里看花,一路挺胸昂首,没有天使指引、先知预告,自以为是,坎坎坷坷。没关系,只要你长大。人活著,好比打开一架摄影机,少年时底片感光,不曾显影,一直储存著,随年齿增长,一张一张洗出来。──王鼎钧
《关山夺路》是王鼎钧回忆录第三部。王鼎钧说:国共内战的题材怎么写,这边有这边的口径,那边有那边的样板,我没有能力符合他们的标准,只能写我自己的生活、思想,我应该没有政治立场,没有阶级立场,没有得失恩怨的个人立场,我入乎其中,出乎其外,居乎其上,一览众山小。而且我应该有我自己的语言,我不必第一千个用花比美女。如果办不到,我不写。以下摘自本书:听到过一首歌「左边一座山,右边一座山,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。左边碰壁弯一弯,右边碰壁弯一弯,不到黄河心不甘。」国共好比两座山,我好比一条小河,关山夺路、曲曲折折走出来,这就是精采的人生。──王鼎钧
《文学江湖》是王鼎钧回忆录第四部,记述1979年去美前的30年。他在序中说:我写回忆录不是写我自己,我是藉著自己写出当年的能见度,我的写法是以自己为圆心,延伸半径,画一圆周,人在江湖,时移势易,一个「圆」画完,接著再画一个,全部回忆录是用许多「圆」串成的。王鼎钧在台生活30年,度过青壮时期,为甚么只有一本的篇幅呢?他在序中写道:确实很费踌躇。最后决定只写文学生活,家庭、职业、交游、宗教信仰都忍痛割爱了吧,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文学江湖》。以下摘自本书:「江湖」是当日的情景,依我个人感受,文学在江湖之中。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,缺少典雅高贵,没有名山象牙塔,处处「身不由己」,而且危机四伏。──王鼎钧
编辑推荐
「我后悔说了那些话」王鼎钧说了哪些话? (专访上篇)
「我把作家分三类」王鼎钧:这类作家有悲天悯人境界 (专访中篇)
「我看见世报转型」王鼎钧:包容促进族群和谐 (专访下篇)
采访侧写/王鼎钧 「明月直入,无心可猜」
王鼎钧「谈理想化」一一虚构的可理想化 非虚构的不可以
我也来讲理一一张大春谈「那些启发我的老台北作家」
写到老,真好! 张晓风看王鼎钧:写得恣天纵地的高手
连连看/王鼎钧8本大作 经典文字出自哪本书?







发布评论